我是1946年秋到香港参加致公党中央总部工作的。而参加致公党工作却是早在1942 年在重庆与当时在中共南方局工作的许涤新同志一次长谈后决定的。从此我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我觉得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爱国之路。
从事政党工作,对我来说是从头学起。我少年时期在学期间,在彭湃老师等的影响下,曾参加反帝国主义游行、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马来亚期间,接触到一些华人劳工,他们的苦难生活真不是“九死一生”所能形容的,一般被贩卖去当苦工(被称为“卖猪仔”)的一两百人中,能活着满工的往往不到十人八人,能回国的则少之又少了。在做工的矿山中,我看到矿工们的生活很苦,许多工人都算是“自由之身”了,实际上并不自由,工资本来就少,即使有一点剩余,工头们总要千方百计把它吃掉。矿业主营利百十倍,对矿山设备却很少改善,工伤时时发生,工人中能出矿山过晚年的不多。我任采冶技术工作时,深受殖民主义者的气,使我深深地感到,祖国不兴盛,就挺不起胸膛做人。因此,我决然于1934年回到国内来。1935年秋到四川成都,初搞印刷, 印发过反对日本侵华的一些信息。1936年“西安事变”后,印发过《抗日统一战线》等小册子。1937年我去四川、西康一带山区勘探金矿,到过几段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所到之处总听到一片赞扬红军的谈话,人们称赞红军省吃节衣救济穷人,他们还称赞红军不恃强欺弱,公平买卖。一个陪我们到彝族地区的帮会头子的副官在闲谈中说:“刘军临撤退我镇时放火烧屋,是红军赶来救火,并救济灾民。国民党说红军青面獠牙、杀人放火,谁肯信?”红军长征途经之处,除蒋军和军阀外,多数都说“红军好”。日本大举入侵,我回到成都,于1938年夏与几位共产党员创办一个小型的日报,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我在他们的指引下负责收集有关资料的工作。1939年秋我因本身职业关系,经安南、新加坡、马来亚去缅甸调查中缅货运的状况。沿途在乡亲友好的邀约下,参加一些介绍祖国抗日形势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特别介绍了台儿庄战役和平型关战役。当时敌后根据地日益扩大,全国人民信心日益增强,坚信:只要坚持团结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不料这些活动却得罪了国民党特务,他们认为谈这些事是在替共产党做宣传。我在那种环境下已无法继续工作,只好回到四川。
从缅甸回国后,我感到爱国抗日需要做更具体的工作,因而辞去企业职务到成都全力投入《时事新刊》的工作。这时,蒋帮更加猖狂地镇压爱国力量,于1939年秋在成都制造抢粮事件以嫁害抗日群众,《时事新刊》是被害最惨重者之一,他们抢去全部印刷机,缚去全部住在报社的人员,并于当晚杀害了共产党员朱亚帆,封闭了《时事新刊》的编印处和发行处。我因为住在报社外,于第二天得到好友王季甫通知和帮助,匆匆离开成都。1941年秋我由四川去香港,在九龙东江纵队联络处遇见东纵政委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尹林平)同志。在交谈中,他谈了东纵打击日本侵略军和汉奸的动人事迹,也谈了华侨服务团的爱国革命情况,都令我感动。可是当我表示想参加东纵时,他认为以我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后方工作比在前方更好。于是我回到四川并参加组建起来不久的民主政团同盟。当时我们以各种形式的集会,揭露反动派配合日本侵略军南侵和设置陷阱伏击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当时中共为顾全大局,不能在重庆《新华日报》披露这件事,只登载周恩来的题字“千古奇冤”!我们初期是从国民党的爱国军官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以后才陆续看到一些较详细的文件资料。反动派此举是卖国罪行,全国人民都恨之入骨,从此,抗日力量更加发展了,对共产党更加信服了。
1942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所谓的“国民参政会”,在会上再三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实质上是加强独裁统治,镇压爱国力量,以遂其投降日敌的目的。参加会议的稍有良心的人都大为不满。当时爱国侨领司徒美堂从美国回来参加会议,他很怨恨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接触了进步人士以后。从1936年西安事变,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亲自到西安进行调解,力争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战所表现出的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与蒋介石反动派配合日敌坑害新四军的罪行进行对比,他深感恢复由华侨社团致公堂改组的致公党组织,以团结华侨共同抗日兴国之必要。司徒美堂是致公党创建人之一,当时在重庆的原致公党人陈其尤也赞成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就在上述背景下,许涤新同志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许涤新分析了我的亲身经历后,说明了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需要一些人参加工作,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道理。许涤新还说,黄鼎臣也决意参加致公党的工作了,并说中共各地组织会给予致公党具体帮助。这些话,给了我信心和决心。
(选自《此心安处是吾乡——广东致公文史资料选编》,2025年6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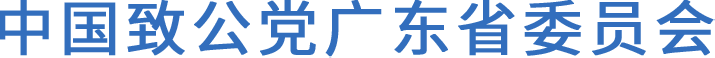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致公简介
致公简介  致公新闻
致公新闻  组织工作
组织工作  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  参政议政
参政议政  对外联络
对外联络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资料中心
资料中心  当前位置:首页 > 宣传工作 > 党史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宣传工作 > 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