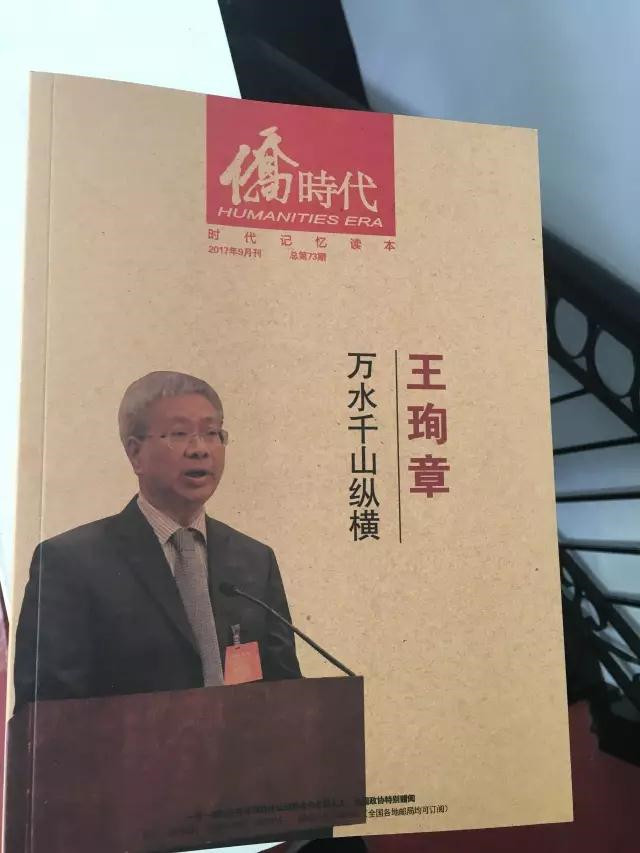
王珣章,1951年7月生,海南海口人,归侨,1996年9月加入致公党。英国牛津大学病毒
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
任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下午的阳光,透过黝黑的木窗洒进来,斑驳的砖上,一张小桌,三两椅子,聊聊他的家
国往事,与这一旧楼的几许烟雨。
好多年前,在《侨时代》还是《侨星》的时候,编辑部就开始手写一页页名字,赠给广
东省内的涉侨部门。王珣章,一个手写了许多期的名字。
今天,他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编辑部。
朴实、儒雅的知识分子气质,与我们想象的官员并不一样。
《侨时代》并不想笨拙地记录每一个人的生平往事,但是他的故事,娓娓道来,像一幕
幕电影,又像是一部纪录片,记录着归侨与中国这一路的荣辱与共。
印尼往事
印尼有多少个岛?有人笑说,印尼自已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岛。
在这个由无数小岛组成的国家,中国人移居印尼的历史悠久,17世纪西方殖民者大举入
侵东南亚之前,印尼已有华侨华人近万人。荷兰殖民者统治印尼期间为掠夺当地资源,大
批招引华工前往,达数十万人。1949年,印尼独立时,华侨华人已达200万。
1951年,王珣章出生在印尼,成为当时在印华人的200万分之一。
他仍记得,自己在印尼的童年时光,周边弥漫着“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分。小孩
因此而分成两派,不同“派”的小孩不会玩在一起,他们甚至是敌对的,相互吵架、打
架。
在那个年代,这是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中普遍存在的状况。
因为祖籍海南琼山,父母在革命老区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这一个家庭一脉相承地深深地
爱着自己的祖国。
少年时候,他与一帮少年时常走进当地的中国领事馆,观看关于中国的各种电影和纪录
片。巍巍中华,绵延江山,一点一点印在少年的心头上。
他就读的小学,是当地的华文学校。后来,他才知道,他的老师们,很多都是优秀的共
产党员。
“三十年代,有不少共产党人,因为各种理由来到南洋各种地方,他们都有文化,所以
都在当地办华文学校,教书。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的教导主任,是以前在祖国游击队的政
委。”
正是这些共产党人在异国他乡洒下了爱国与中华文化的种子。
14岁,他初中毕业。因为学习成绩优秀,他被中国驻当地领事馆选中,免费保送到广州
华侨补校学习。
与他同行的,还有甄选出来的9个优秀少年。
因为是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又是品学兼优才获得的荣誉,父母对他的机会都感高兴。
因为年龄尚小,他还没有护照,他把护照附在了大一点的侨胞的护照上面。
在前往印尼首都时,当时的爱国社团琼州社也出资支持这位归国读书的海南籍少年。
在雅加达,他们终于坐上了从印尼开往中国的轮船。
那一艘轮船,名为“光华轮”。
光华者,光我中华。光华轮,是新中国第一艘自营远洋船舶,是中国远洋运输事业诞生
的第一个产儿。在艰苦的岁月里,她和驾驭她的英勇海员们在当时风波险恶的南海和印度
洋上谱写了一段壮丽的诗篇。
是时为1965年,王珣章在光华轮上,真正开始了自己万水千山的第一程。
风急雨翻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到60年代末,前后20年的时间里,人数不下十万的海外华侨子弟,
纷纷回国升学,以“学好本领,建设新中国”为共同的目标。
这一股“回国升学热潮”,催生了一种华侨史上有名的学校:华侨补校。首先是由辛亥
革命老人、中侨委主任何香凝题写校名的“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其后,华
侨补校在广州、厦门、昆明、武汉、南宁、汕头等地陆续开设。
王珣章入读的,便是广州华侨补校。
正是立志学本领、建设新中国时候,一场席卷中华大地的时代命运轰然展开。
在华侨补校就读了一年后,文革开始。华侨补校被作为“修正主义”受到批判,最后被逼
撤销。
他年龄小,学业成绩又好,老师动员他和班里的几位同学到广州读高中。
但那时候,连大学都纷纷被关闭,他不知道这一路走下去会是怎样。彷徨中,与大多数
同学一起,在1968年第一批下乡到了海南岛。
海南,是他梦里的故乡。
但那个时代里的海南,是穷山恶水一片片。在广阔原始的大山里,他们手足无措。
住的是自己用泥巴混稻草新盖的茅草房,睡的就是简易的木板,风寒露冷。每天都是没
日没夜地砍芒草、割橡胶,与飞虫蚂蝗斗争,与皓月夜星为伴。
稍有点工闲时间,他捧起书本再复旧梦。
1969年,部队接管农场,成立兵团,他自学了全部的高中课本。
凭着这一股勤奋劲,他被兵团选送到中山大学生物系学习。
毕业后,他被分到海南岛的热带作物院(研究院)。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王珣章再以优异的专业成绩和外语能力被中山大学录
取。
这时,离他回到祖国已过去了十三年。这十几年,他作为一名归侨少年,与这片土地上
的大多人一样,感受着时代的脉搏。
有两位伟人的讲话,改变着他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
一位是毛主席的刊登在《人民日报》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
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
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另一位是小平同志关于高考的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
考!”
不同的是,在时代的风急雨翻中,他比别人更多了些坚持。
再别万山
就在刚过去不久的六月,《侨报》登了一篇关于中国留学生逾期不归的统计文章。该报
道引用了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2016年逾期不归的中国留学生的调
查,指出:“有7545名中国留学生,在签证过期后续留美国,人数高居所有国家之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济基础和道德观念,只是,当我们再回首,80年代的留学生,他们在
面对“要个人幸福还是家国情怀”这个命题时,他们选择的坚定,却让我们缄默。
公派留学,曾经是一个有着温度的词汇。
背景是80年代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和西方已完全隔绝了三十年,和苏联、东欧也断绝
来往二十多年了。在这几十年中,中国人没有谁敢梦想今生今世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更
不要说去海外留学。
1980年,王珣章,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能被公派出国留学的一名学子。
十几位同学一起,从广州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到俄罗斯,转荷兰,再坐船抵达英国。
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有的正是年少风华,有的已结婚生子,有的已工作多年。
是时的王珣章,刚刚在木棉花开的广州,认识了自己的妻子,组成家庭。妻子是同学的
朋友,是华南师范大学的老师,与他一样是那个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
见面之后,彼此觉得可以,便相约看了一部电影。电影是《五朵金花》。
那是一部讲述一对白族青年在云南大理三月街从一见钟情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电
影。
新婚燕尔,便要踏上出国留学之路。在那个年代,家属并不能跟随留学共赴海外。于
是,他再次孑然一身,别万山而去。
就像当年,他与同学少年,万水千山外坐船回到中国一样。
“我们去到莫斯科的大使馆,他们管我们的吃住,又帮我们买火车票到荷兰。到了荷
兰,驻荷兰的大使馆又帮我们买去英国的船票。”
如此细说这些细节,实在是想回味那个年代,一批学子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希望而全国人
人用力帮扶的记忆。
据说,当时中国一万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十几个出国
少年,都暗下决心,学成归来一定要努力报效祖国!
“那时候大家的思想都很单纯,因为我们是公派的,所以都觉得回国是理所当然的,是
必须的。若有谁留恋他乡不回国,人家都会说他,必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
在英国,他就读的是牛津大学,攻读的是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
与那个年代的留学生一样,他一方面融入当地的语言,一方面勤奋地听课、做实验、查
资料、写论文。
四年后,他学成,兑现诺言一般,再次归来。
高峰远滩
1984年,英国留学归来的王珣章,回到了中山大学昆虫研究所。
昆虫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但他钻研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他在中大开辟了一个全
新的研究领域,即昆虫病毒基因工程的研究。据介绍,这项研究是1973年世界上才开始发
展起来的基因工程技术。
他组织了自己的学术队伍,并最终在这个领域,创造性地“应用异源病毒基因重组出含
外源基因的昆虫杆状病毒”,“使我国昆虫病理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媒体以“生物学王国一骄子”为题来报道他。
在1987年开始,他获得了美国洛克菲勒生物工程职业研究基金,连续三年定期赴美国研
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生物学精英一起交流、工作。
1995年,他以44岁的年龄,被提拔为中山大学的校长,一时在教育界引起轰动。
一方面,他是新中国以来中山大学最年轻的校长,一方面,也有人不免惋惜一名科学家可
能从此就要被行政杂务挤占了科研的时间。
而今网上有人发表评论:“中大自王珣章执掌以来,在青年人才路线一直落实得很
好。”
在他的带动下,中大的学术气氛更加活跃,中青年学者群体成绩斐然,引进的博士逐年
增多。
1997年,王珣章当选为致公党广东省第八届委员会主委,致公党中央第十一届委员会副
主席。
1998年,王珣章当选为政协广东省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
他从此走上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在另一个舞台上,继续着当时印尼归来时的报国之
志。
他在各种协商会、座谈会上建言献策;在党派工作中发挥自己的科研力量。
岁月荏苒,当初的那个风华少年,如今两鬓已斑。
他成就了几个“最”:1985年,他34岁,成为广东省最年轻的副教授;1990年,他39
岁,又成为全国生物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95年,他44岁,荣任中山大学校长,又
是全国34所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一楼烟云
这里是广州荔湾多宝路的221号。
在四楼,古老的房子里,王珣章说,当年他想起一封信,也想起了这一栋楼。
那一年,王珣章和致公党广东省委一些同志到重庆去参加某个学习座谈会。在重庆,他们
参观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回来后,他自己觉得深受启发。
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在重庆接触了很多各民主党派的友好人士。重
庆的陈列馆便以此收集了许多文物资料,陈列展览的效果非常好。
王珣章便想到,当年毛泽东主席给在广东的致公党中央党部的陈其尤同志写了一封回
信,信封上的地址,便是这旧楼――致公党中央党部在穗的旧址。
当时,因为一些特别原因,旧楼已租给别人商用。
能不能去看看?能不能收回?
随之而来的,是产权等一堆历史遗留问题。
但是,这里是全国8个民主党派中,唯一一个在广东留下的总部旧址,意义特别。这
里,是致公党从海外到国内的重要见证,是中国致公党初期一众同仁共同奋斗的记忆。
为此,他与省委一些同志沟通,并去克服各种障碍。陆陆续续,曲曲折折,不觉已经年。
2017年,陈列馆终于如愿成立。
他说,感到很欣慰。
就像当年,他父母知道他有机会回国学习一样欣慰。
一样的,是一份侨意,一份祖国心。
他说,前不久在山东开会,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同志还特意提到这个展馆,万主席参观
了之后也很有感触。
他说,这里储存了太多的致公人的记忆。初期时,一批批致公党前辈在这里风雨与共;
八十年代,没有多少房子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到机关来上班,住在这里,这里等于也提供
了一个当时致公党人的集体宿舍……
时间已然是傍晚,斜阳有余晖。
目前刚卸任致公党广东省主委一职的王珣章,又开始担任广东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
谊会首任会长。他说,这一辈子都在做与侨海有关的工作……
说起华文教育,他说自己的孙子正在加拿大,也在学中文……
恍如,看到当年在别国的他。
万水千山走遍,归来仍是爱国少年。
(转自杂志《侨时代》)

 首页
首页  致公简介
致公简介  致公新闻
致公新闻  组织工作
组织工作  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  参政议政
参政议政  对外联络
对外联络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资料中心
资料中心  当前位置:首页 > 宣传工作 > 致公风采
当前位置:首页 > 宣传工作 > 致公风采